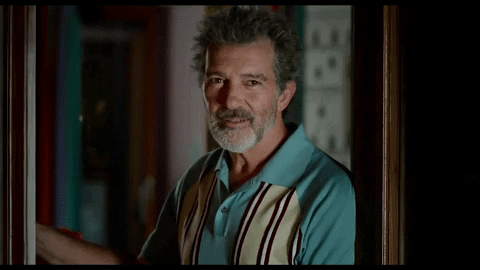愛情雖然苦口,或許是最終的良藥;唯有真的愛上了,我們才有機會真正思考「時間」與「健康」這兩個在情傷時最常被拿來踐踏的事。
兒時記憶與中年交織
開場畫面從冰冷的游泳池底開始,一名叫做薩爾瓦多(安東尼奧班德拉斯 飾)的中年男子,在水底下閉著雙眼沈思。
沈浸在這好似羊水的初生記憶裡,他到底在想什麼?
在閉氣好似瀕臨死亡的走馬燈裡,他回想到了什麼?
母親。

《痛苦與榮耀》片中母親,由金獎得主潘妮洛普克魯茲演出
童年與母親的回憶,她與村婦阿姨們在河邊洗衣服,小薩爾瓦多用稚嫩無邪的眼神,望著正在吟唱、翩翩起舞的母親...,瞬間拉回現實的瞬間,男孩與大叔的對比衝擊,正片由此開展。
好一個溫柔又撕裂的開場,這,是我們熟悉的阿莫多瓦嗎?
中年失意導演的旅程

薩爾瓦多是誰呢?一位曾經風光一時、如今中年失意的電影導演,遲遲沒有新作品發表,他似乎失去創作的動力與能量、心頭好似有個解不開的結;加上關節的痛楚以及隨年邁帶來的病痛,讓他分不清楚究竟自己是無法再寫、還是不知道要寫什麼,又或許有什麼更深層的、是否有勇氣寫出來?
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這比死刑還痛苦。畢竟電影對他來說是生命,而創作更是他賴以為生的氧氣。
「他現在的演技比三十年前好。」
「那是你看事情的眼光變了,電影還不都是一樣的嗎?」
許多我們年輕時在意或過不去的事,在白髮蒼蒼之際,總能偶獲開示;倒不是全然地妥協,而是愛情的奮不顧身(或遍體鱗傷)、身體痛楚、生離死別的體驗,讓我們看待同樣一件事情,有了截然不同的解讀。

阿莫多瓦的畫面,總是不缺配色鮮明多彩的房間
即使生老病死並不是什麼太歡欣鼓舞的題材,阿莫多瓦仍舊用五彩繽紛拼貼出薩爾瓦多的病症、藥丸、角色服裝,以及那偌大且極具酷兒品味的公寓,不僅隱隱對應了他的性向,更襯托出他獨身的寂寞。
在片中,薩爾瓦多花很多時間在睡覺,他總是閉著眼睛。我在那些看似無意義的沈默時刻,好似看見了自己父親的影子。「他一定有很多悔恨的事吧?」每每看著坐在輪椅上的父親,他眼角眼淚眼油分不清的液體、總是選擇緊閉或低垂的雙眼,我總覺得除了生理上的疲倦,父親肯定不斷地在回首過去;而薩爾瓦多,肯定也在悔恨些什麼吧?

言外之意:男體慾望的啟蒙

這齣戲在許多小細節上都頗具用心,例如劇院牆壁上貼著一張海報,那是美國知名同志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的劇作「熱鐵皮屋上的貓」(上圖,後被翻拍成電影《朱門巧婦》);故事裡其中一位男性角色布瑞克(Brick),因為誤會自己同性愛人與妻子有染、而導致同性戀人自殺,自始至終無法面對自己的妻子;雖是短短一個畫面佈景,卻也令人咀嚼再三。

片中充斥著這樣看似無心、實則有意的線索,舉凡當年母親帶著他來到異鄉找父親,在荒涼的鄉下,他與一位俊美卻不識字的水泥匠畫家匆匆一瞥,啟蒙了薩爾瓦多對男性身體的慾望,也啟發了他後來的創作《第一個慾望》;小薩爾瓦多指導水泥匠寫字,小手握著大手,一筆一畫勾勒出文字;或許拍片者無心,看片者有意,我著實覺得這些鏡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含蓄與性感,更別提那段令人臉紅心跳,水泥匠在客廳沖澡的畫面,小薩爾瓦多發燒與發騷已經傻傻分不清楚,青春的迷情,卻能如此無暇純淨地展現出來,阿莫多瓦的功力實在高明。

「我童年的電影記憶,總伴隨著尿味、茉莉花香...和夏日微風。」
這句話來自薩爾瓦多的散文〈成癮〉,某種程度上,也是我最喜歡的台詞之一;短短幾句話就把童年的味覺、嗅覺和視覺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來。這篇散文意外被演員朋友發現,立馬要求擔任以該散文改編的劇本主角;卻被薩爾瓦多回絕。
「那你為何而寫呢?」演員問。
「我寫是為了忘掉這些事,別說了。」他默默地說。
〈成癮〉這個幾近自傳式的愛情故事,終究還是上演了;當薩爾瓦多把劇本交給演員後,念茲在茲的幾段話令人印象深刻:「不能過於煽情,要控制情緒、忍住哭,很多演員一逮到機會就會天花亂墜地宣洩情緒;事實上,好演員不是很會哭的那種,而是忍住不哭的那種。」不僅對應到他年長後的心境,更隱晦地與哈姆雷特對表演的看法有所呼應:「特別注意一點,你不能越過自然的常道,因為任何過分的表現都和戲劇的原意是相反的...要是表演得太過分或太懈怠,雖然可以博外行觀眾一笑,明眼之士卻要因此而皺眉。」對於真實與虛幻、戲劇與人生、壓抑與解放,阿莫多瓦透過對「表演」這門技藝的評論,表露出別具深刻的體悟與省思。

而劇本裡頭所提及的愛人,竟也在現實生活中交會。這一別數十年的愛戀,重逢的情節極為動人;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因對方吸食毒品而分手,晚年的薩爾瓦多反而開始吸毒;看似為了藉以舒緩身體的痛楚,但或許也透過這樣的「自虐」,來表達對當年這場無疾而終戀情的一種無聲抗議吧?
坎城影帝

完美演繹深沉與痛苦,安東尼奧班德拉斯以《痛苦與榮耀》勇奪坎城影帝、並入圍奧斯卡影帝提名
安東尼奧班德拉斯舉手投足都賦予角色極為寫實又細膩的肢體感,舉凡上下計程車的重心移動,藥丸掉落地板時,必須先拿軟墊放地板才能跪地,與舊戀人重逢的微笑與傷感...等等,都能看到他詮釋角色的用心與深刻,尤其與愛人重逢的戲實在是演得太好了;兩人的親吻,曖昧、也不曖昧,雖然遺憾、卻也輕盈昇華;道別後衝回房間準備吸毒的眼神,那種佯裝堅強後的慌張,以及亂了手腳的脆弱,即便只有短短數秒都讓人感同身受。
愛這件事啊,不就是不斷在假裝堅強與默默脆弱之間徘徊作戰嗎?(至少天蠍座是這樣啦)他以本片獲得坎城影帝的殊榮,可謂當之無愧。

愛是良藥
愛情雖然苦口,或許是最終的良藥;唯有真的愛上了,我們才有機會真正思考「時間」與「健康」這兩個在情傷時最常被拿來踐踏的事;剩下的歲月還能與愛人廝守終生嗎?想要為那個人變得更健康,只為能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與舊情人揮別後,薩爾瓦多重新振作起來面對心魔。
在醫院等待看診時,薩爾瓦多不經意地望著天花板那片人工繪製的天空,恰恰與童年鄉下舊家那片天井藍天相互呼應;當年在真的藍天底下覺得自己被困住,如今即使在虛構的天空下坐著,心裡的結開了、反而比任何時候都開闊;阿莫多瓦說故事的方法雖不隱諱,卻總有種讓人會心一笑的巧妙。
自傳?

安東尼奧班德拉斯在《痛苦與榮耀》中,儼然就是導演阿莫多瓦的代言人
在某個訪談裡,即使阿莫多瓦口口聲聲說對於執導自傳式的電影毫無興趣,但男主角安東尼奧班德拉斯活生生就是穿著阿莫多瓦本人的衣服入鏡,也的的確確在阿莫多瓦自己的公寓裡頭取景;導演悠悠地說:「我也不諱言現實與生活間界線的模糊,所以你們儘管發問吧,我不想再躲躲藏藏了。」事實上,阿莫多瓦從未躲藏過,從他過去的每部影片裡,我們或多或少都能瞥進他內心多彩荒誕交織錯亂又幽默的一面;只不過這部《痛苦與榮耀》,少了花枝招展的粉飾,多了一份誠懇真切,也讓這部影片更深切動人。
戲如人生,與過去告解

接近電影的尾聲,薩爾瓦多回憶與母親的談話:「媽媽,很抱歉我沒有成為妳想要的兒子...以前你常說『這孩子不知道像誰』,你的語氣裡並沒有驕傲......我越是做自己,就越讓你失望,真的非常對不起。」
阿莫多瓦曾在訪談中表示:「啊,的確,我從來都不是父母親想要我成為的那個樣子;我的意思是說,雖然我知道他們很愛我;但,我的確很早就察覺到這個事實......但我從未責怪過他們,我父母生於十九世紀的保守鄉村,二十世紀的時候生下我這個猶如二十一世紀產物的兒子。」
根據阿莫多瓦所言,他的父母親希望他留在鄉下並在銀行工作,也真的幫他物色好了職務;還好阿莫多瓦毅然決然地「逃跑」,否則世界電影史的損失可慘烈了。而電影最後那段虛實翻轉,成功地將整部電影化作一個彷彿無限大的人生循環;或許,這是導演在晚年對於生命的一種謙卑與想望吧?又或許,他希望能夠透過這部電影,跟記憶裡的母親和解。

訪談席間,記者問阿莫多瓦,如果這個住在鄉下的小男孩從時間光譜的另一端,來看你如今的成就,他會說什麼呢?
「誰是那孤單獨身的老人啊?」阿莫多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