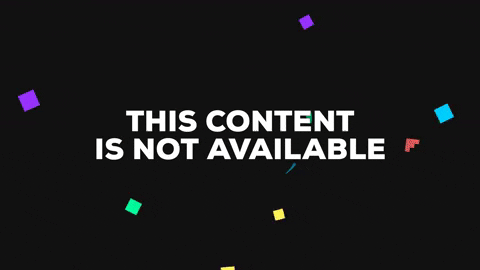無論是出生,或是出櫃、亦或出走,都是一種出發。只願,我們在短暫的人生裡,都能夠恣意地跳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生命。

那雙腿,生來就是要跳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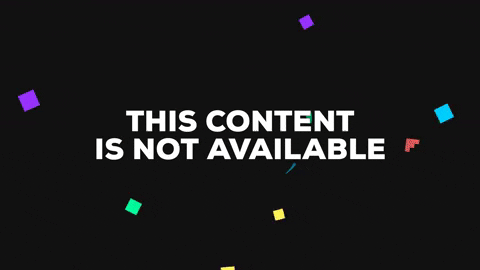
從電影的開場畫面,我們就看著男孩蹦跳,那個雀躍,那個無畏,即便是追出門口尋找祖母的那雙奔跑的腿,都在在顯示,這個男孩生下來就是要跳舞的。短短開場五分鐘,編導便把這個以挖煤礦維生的工人階級單親家庭、祖母輕微失智以及比利與身邊環境的格格不入,建構得相當清楚。主人翁比利從來就不是聽話的孩子,當演奏到一半的鋼琴被父親喝斥蓋上之後,他馬上掀起來小心翼翼地繼續彈著,埋下他始終無法違背自己心意的伏筆。

當我們真心喜歡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是知道的

因緣際會下,比利參加的男孩拳擊俱樂部碰巧必須跟一群芭蕾舞者共用體育館,他舞蹈的啟蒙就此展開。人的一生中,似乎總需要一位導師推自己一把,芭蕾舞者的指導老師,威金森太太,就在這樣的機緣下,結識了比利,也看到了他的潛力。
「你欠我五十便士。」下課之後,威金森太太追上比利。
「我沒有。」
「下星期上課帶來吧。」
「不行,我要上拳擊課。」
「但是你打得很爛。」
「我才沒有。」
「我以為你喜歡跳舞。」威金森太太吐了口煙,看似不在意,其實心裡扼腕。

諷刺地是,有時候承認自己喜歡的事情,竟是如此不容易。但其實我們是知道的。從那一刻起,比利的跳舞魂開始蠢蠢欲動,但現實生活中,父親與哥哥都是極為保守且視舞蹈為無稽之談的傳統男性,這場家庭革命是勢在必行。

某晚睡前,比利問睡在一旁的哥哥: 「東尼,你有想過死亡嗎?」 「閉嘴。」身為罷工激進份子的東尼,想都沒想就堵住比利的嘴。但這一問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唯有真正思考過「死亡」,不畏懼它,我們才有機會真正的活一遭。比利在那一晚,透過這一個簡單的提問,把他青春又早熟的掙扎,表露地一覽無遺。

最暴力的美學:芭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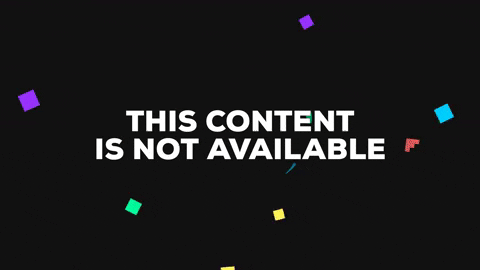
我最喜歡的段落之一,無非是芭蕾舞課與工人示威抗議的對剪畫面;除了優雅與暴力之間的對比令人玩味之外,更隱晦地提出一個大哉問:什麼是跳舞?不就是一連串有意識、無意識的自由意志動作所組成的嗎?如果真是這樣,那罷工人潮這一連串推擠、揮舞手臂的抗議行動,何嘗不是另一種「舞蹈」?再者,芭蕾被視為高貴典雅的藝術形式,但同時也是人類對自己的身體所能做出最「暴力」的行為:完全違背人體工學,踮腳、縮腹、撐托…在如此「殘忍」的行為之下,我們發掘了「美」;暴力與美麗之間的關聯,往往就在一線之隔。

「像電流一樣…像鳥一樣…整個人都消失。對,就像電流(electricity)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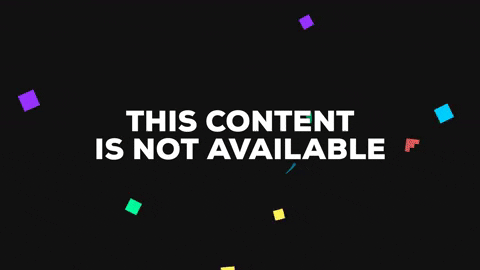
皇家芭蕾學院的評委問比利,跳舞時是什麼感覺。在由艾爾頓強改編成的音樂劇版本裡,這個橋段轉化成一首歌曲:《電流》,裡面有一段歌詞是這樣的:
It's a bit like being angry 有點像是憤怒
It's a bit like being scared 又有點害怕
Confused and all mixed up 好像是兩者混在一起
And mad as hell 而且極度瘋狂
It's like when you've been crying 很像是你一直哭
And you're empty, and you're full 哭到你整個人都空了,但你又被填滿
I don't know what it is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It's hard to tell 很難描繪
這或許是電影裡頭最平實,卻又最觸動人心的一段回答。劇中充滿「權力與威望」的學院評委們,坐在富麗堂皇卻冰冷的甄選室裡頭,遴選來自英國各地的小舞者們。那些自以為是的提問,在與比利的回答對比下,更顯得極度荒謬虛偽。長大之後,我們似乎需要理由來支持每一件我們認為有意義的事,然而我們都忘了,能牽動我們心跳與呼吸的事,哪需要理由呢?在感動於比利的回答之餘,我們也不要忘記,不要變成自己討厭的大人。
編劇李・霍爾(Lee Hall)的切身體驗

女孩問:「會想念母親嗎?」比利說:「其實不太會,突然想起她的時候會難過,有時候會忘記她其實已經不在。」編劇李・霍爾精準且節制地描繪失去母親的男孩最誠實的想法,不煽情且樸實動人。當比利與舞蹈老師威金森太太分享母親生前寫給他的信時,即使他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但當威金森太太說: 「她一定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 「沒,他就是我媽。」比利說。

最珍貴的東西,從來都不需要是最特別的。它之所以珍貴,在於它就是它自己。比利也是這樣,他並不是萬中選一的天之驕子,他之所以跟別人不一樣,就是因為他「做自己」。編劇李・霍爾不斷地將這一個訊息透過各個橋段傳遞給觀眾,他以本片獲奧斯卡、英國電影學會等大獎提名最佳編劇,並榮獲英國獨立電影獎最佳編劇,可謂當之無愧。八年後這部作品被改編成音樂劇,音樂由艾爾頓強操刀,詞和劇本仍舊由李編寫,更於09年獲得東尼獎最佳音樂劇劇本的榮耀。

李・霍爾在某個專訪中回憶道:「當年艾爾頓強看完電影就提議說要改成音樂劇,我當時覺得這個點子糟透了。」但接下來幾部成功改編自電影的音樂劇輪番上演,改變了李的想法。 「好吧,如果真的要改,一定要比電影精彩。」李說。「事實上,這個故事跟我成長的背景很像;我來自於蘇格蘭新堡的保守家庭。原本想寫一個立志成為作家的男孩故事,但想想,誰會想要看一個小孩坐在那邊一直寫呢?於是我想到了芭蕾。」李說。

故事就這樣展開了,那是一個保守的礦工家庭,對於男女之間的分際是如此刻板印象地做出分野:男生就該踢足球,男生就應該摔角,男生必須要打拳擊。在李的筆下,比利是如此迷人的角色:他是一個會反駁抵抗的人,他叛逆卻溫柔,如同他的父親ㄧ樣,雖然固執,但對兒子的愛,卻是如此含蓄且壓抑地令人動容。

場景回到聖誕夜的那一跳,比利與友人在體育館跳舞,父親氣急敗壞地衝進體育館,父子對峙,全場屏息。那一刻我們都在想,比利是否會低著頭,讓父親拎回家狠狠教訓一頓?不,比利沒有,他跳了起來,他必須要跳,他要讓父親知道,有太多話,在這樣的家庭裡,無法說,也不能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跳。那一跳,實在是太震撼了。父親看見了;父親與兒子之間的和解,終究,需要這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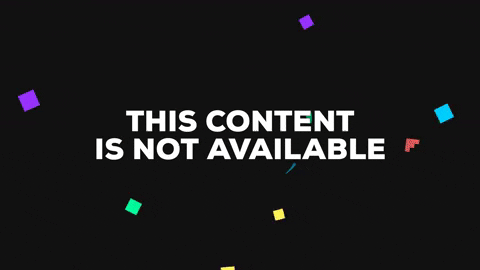
「父親去世前幾年,到紐約欣賞音樂劇的首映,」李回憶著,「我親眼目睹父親『終於理解』,台上的那位父親角色,其實就是他自己。」,他說父親很高興自己就是電影和舞台劇裡的那一個爸爸,因為那個父親最終理解了比利的立場,扭轉了整個故事。 的確,在這部片中,父親的角色寫得特別立體、動人。讀完這篇訪談之後,更能感受李對父親的景仰與愛。

李原本想要寫一個很「小」(tiny)的故事,他萬萬沒有想到,這部片竟然會引起這麼多人的共鳴。但他又何須如此意外,我們不都是比利嗎?我們不都曾經與父母親爭吵,並尋求和解?我們都知道思念一個人的感覺,我們更知道違背心意的那種痛楚與掙扎,我們都記得與親人告別時的擁抱…導演把這些小人物的生活細節,拍得極為細膩真實,筆者看到比利與祖母道別的場景,眼淚意外地奪眶而出:只見奶奶緊緊地抱住比利,然後突然狠狠地將他推出門;那一個推,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氣,愛與力量呢?

幸好,這仍是一個圓滿的故事;如同開場的歌曲所說:「I was dancing when I was out.」或許,我們從出生的哪一刻,就已經在跳舞。這個out,無論是出生,或是出櫃、亦或出走,都是一種出發。只願,我們在短暫的人生裡,都能夠恣意地跳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生命。